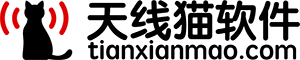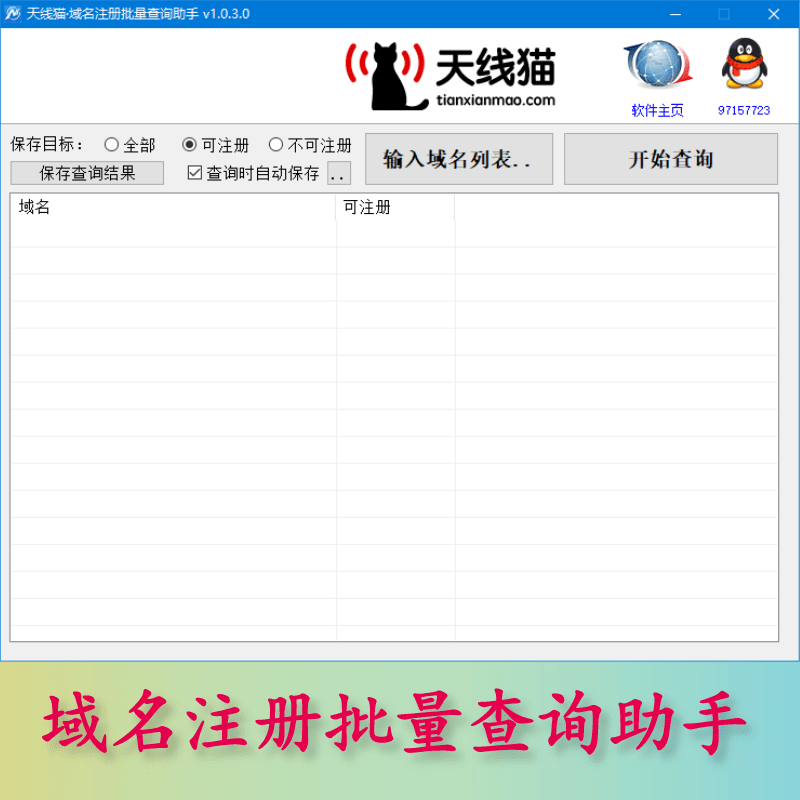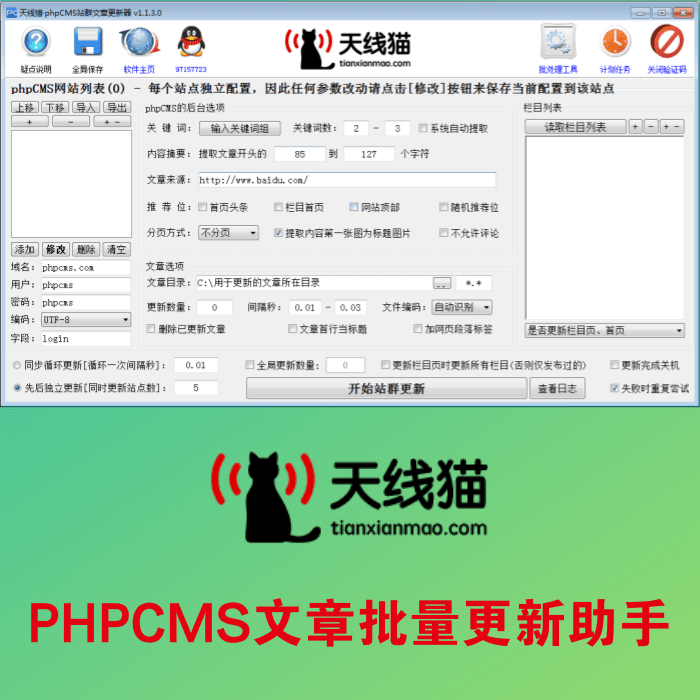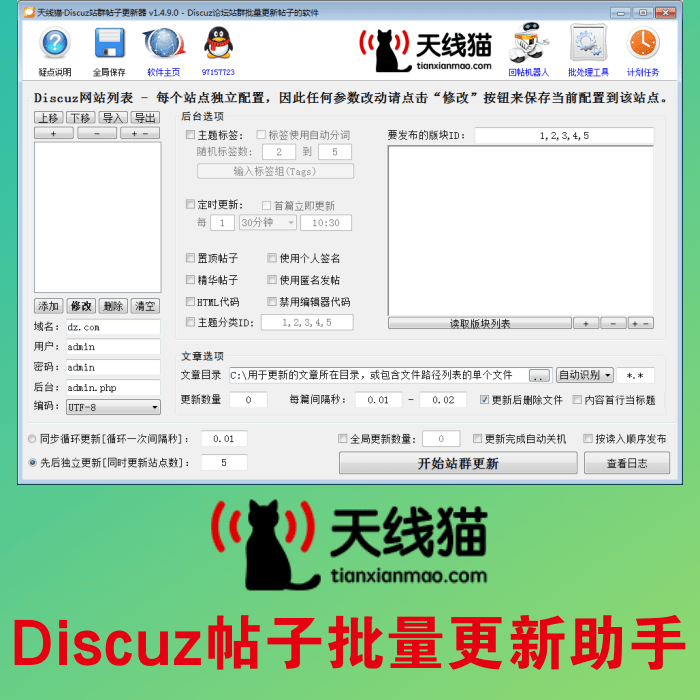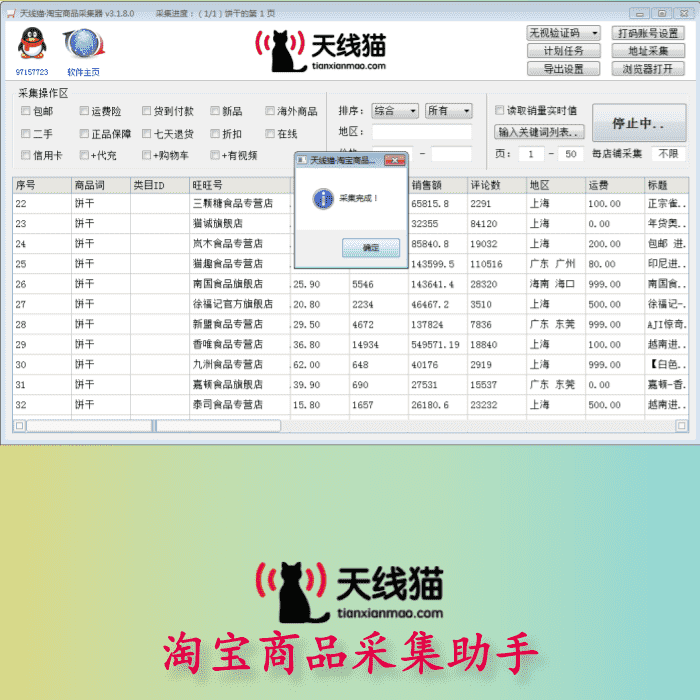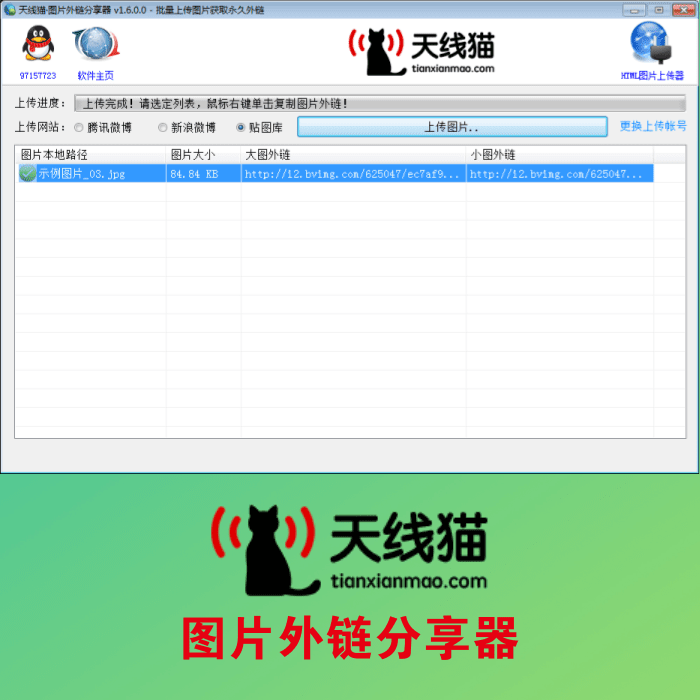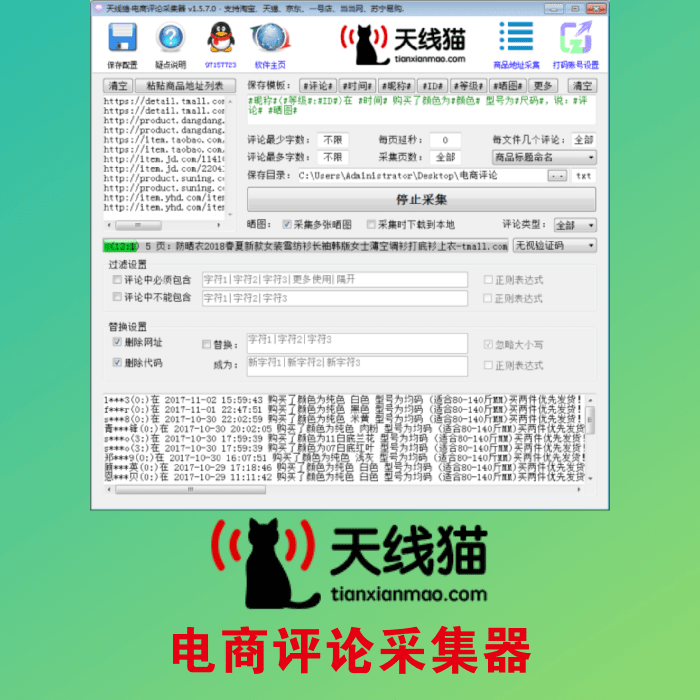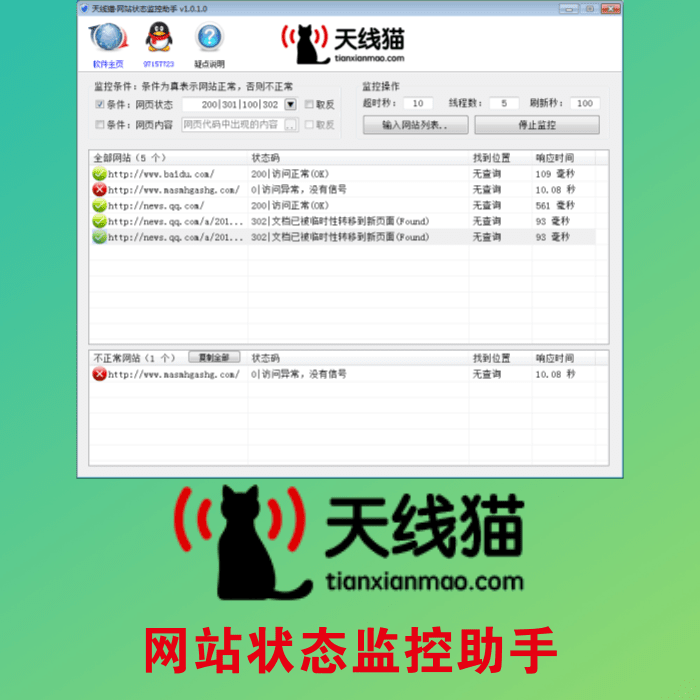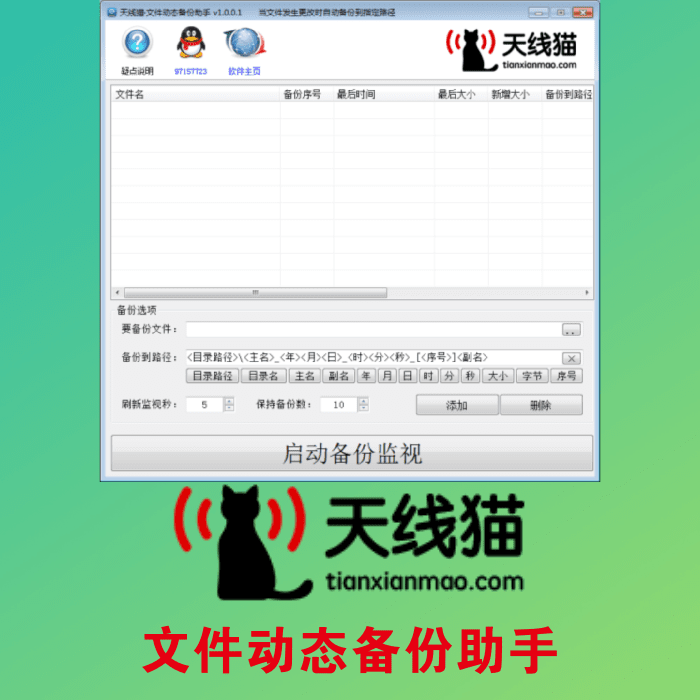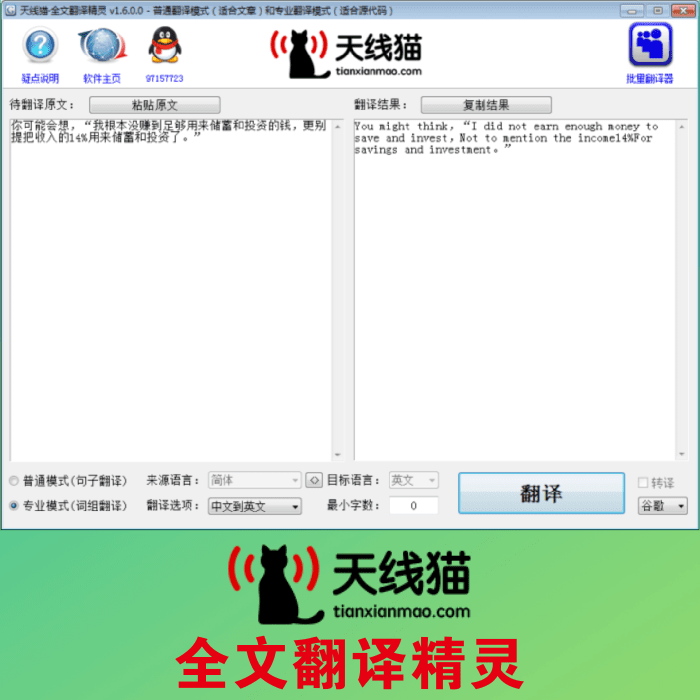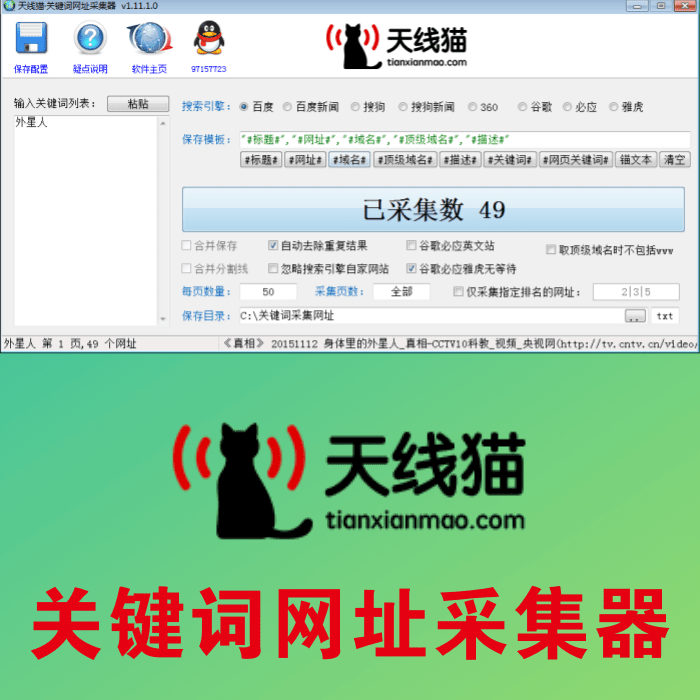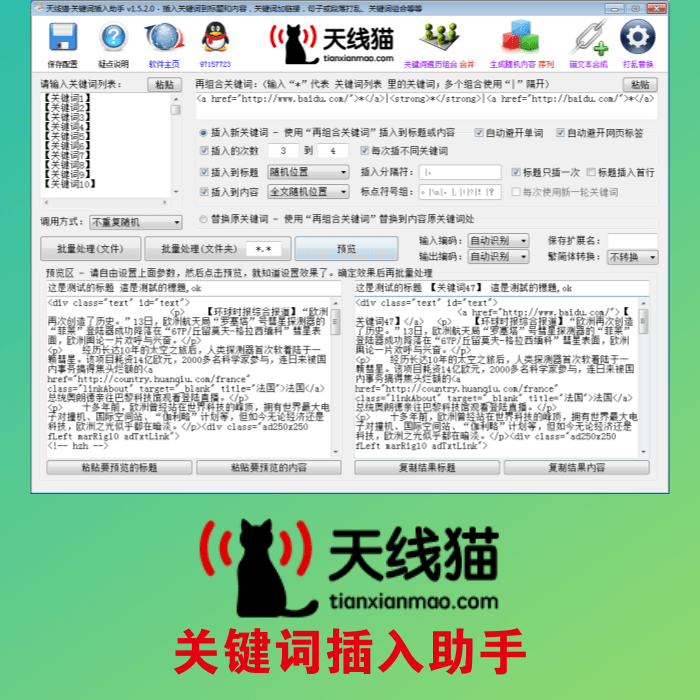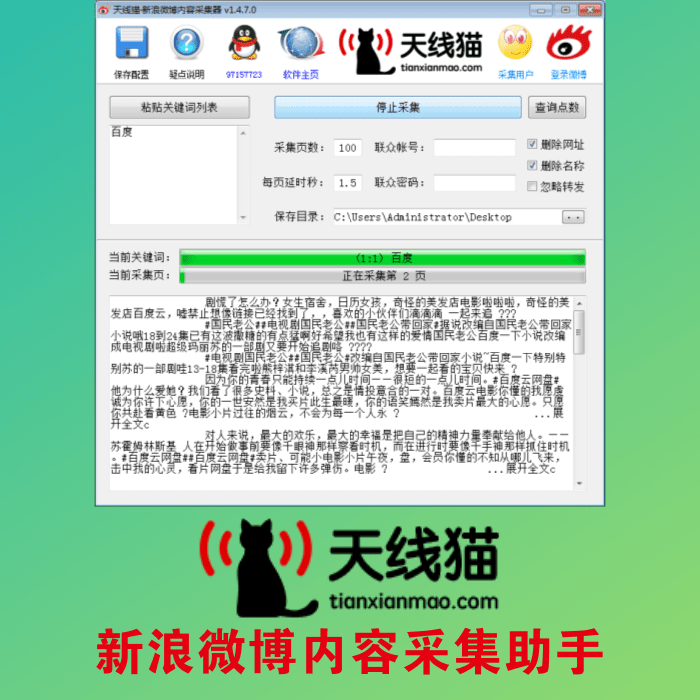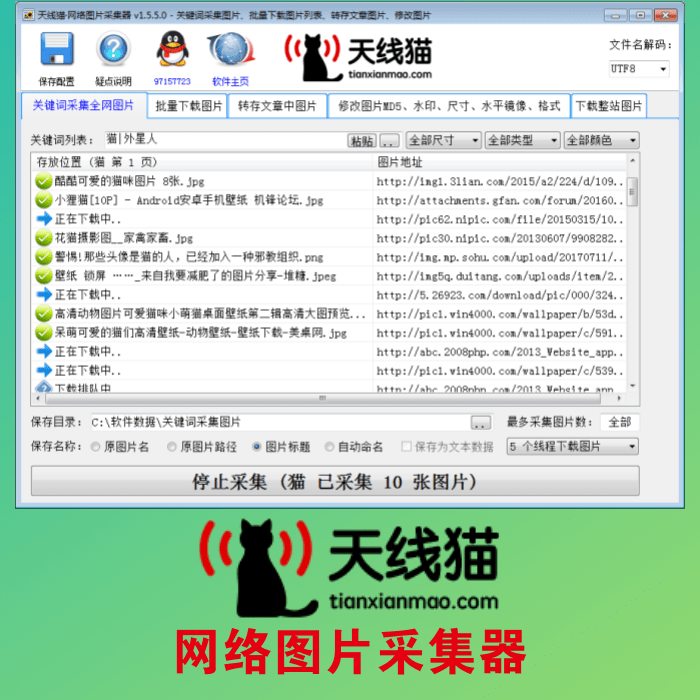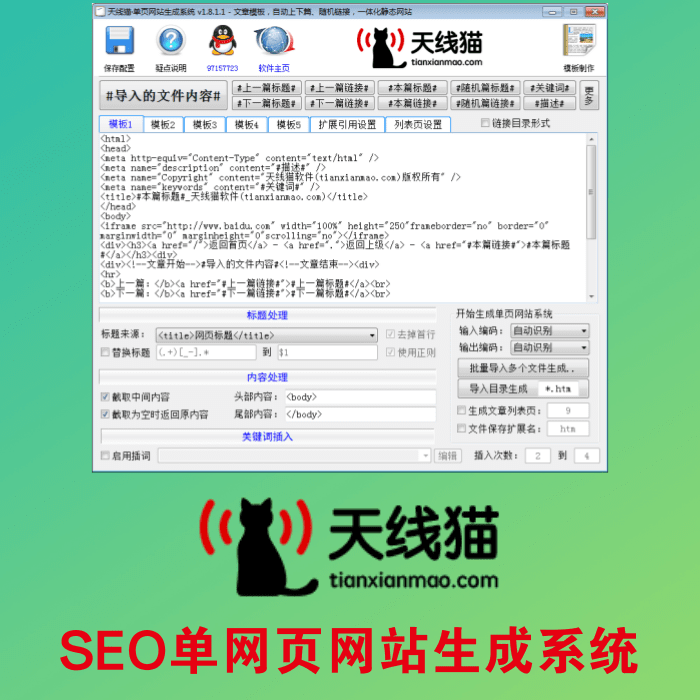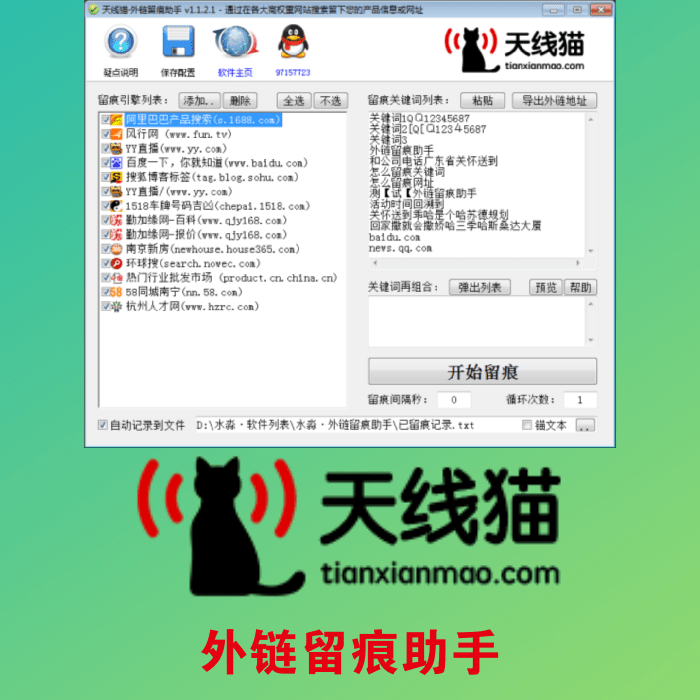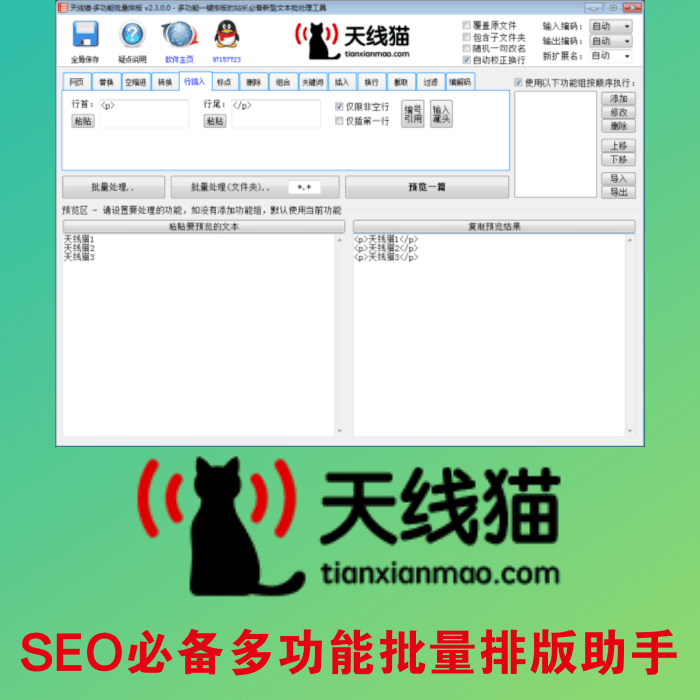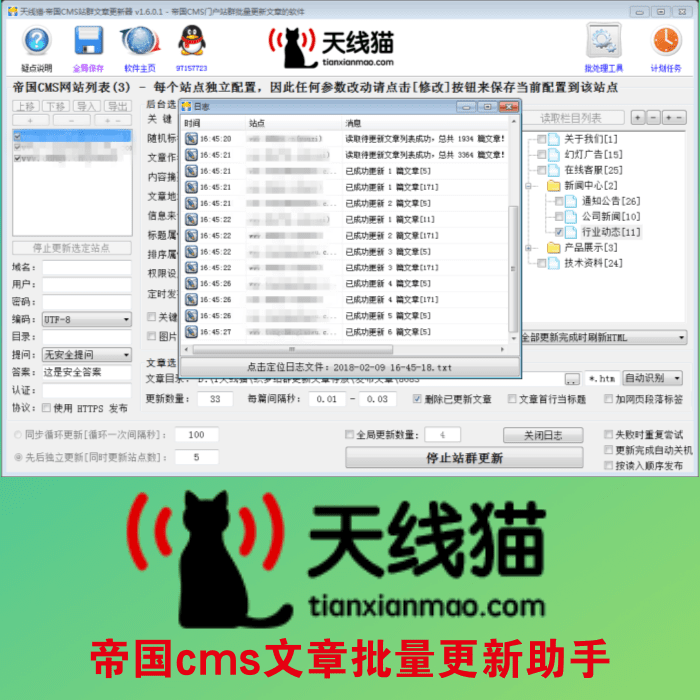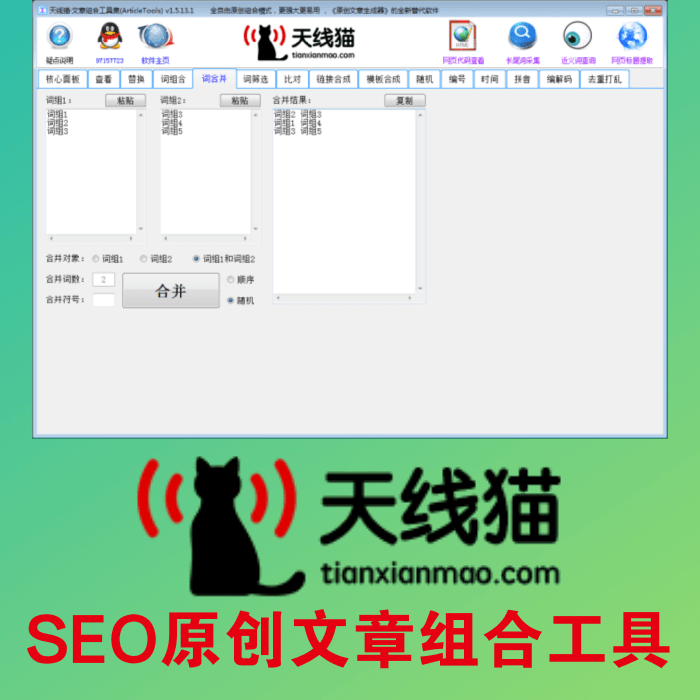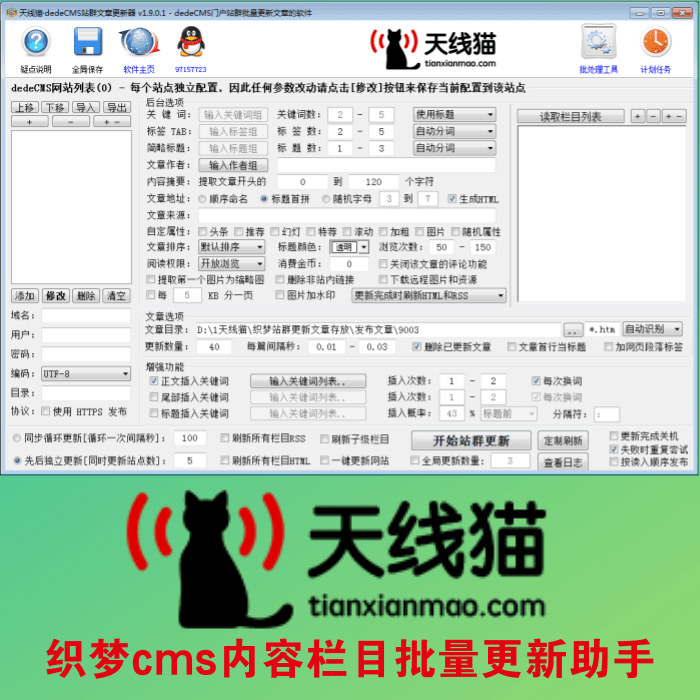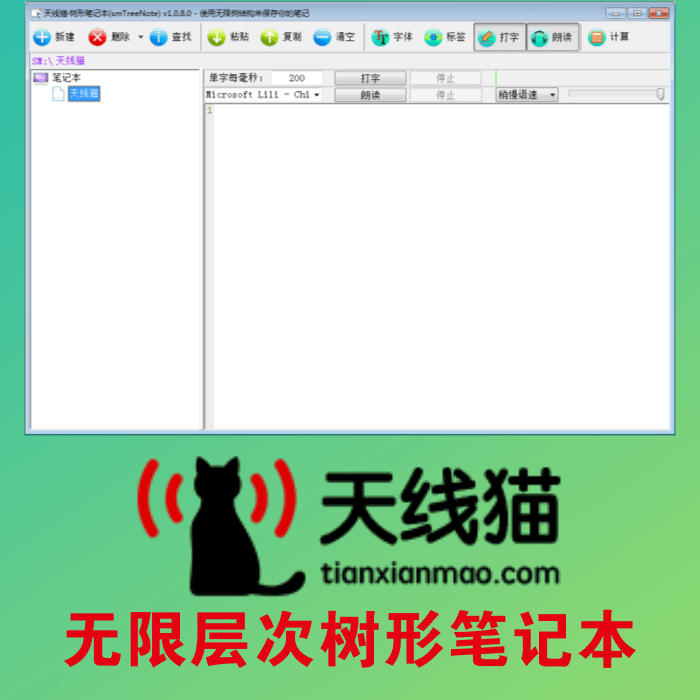《第一次的親密接觸》
這是華語世界第一部網絡小說,作者痞子蔡。1998年3月22日開始在臺南成功大學電子布告欄(BBS)連載,到現在已經整整20年了。
當時,中國的互聯網用戶不到百萬人。對那個年代的多數年輕人而言,《第一次的親密接觸》,也是他們和互聯網的第一次親密接觸。
我第一次知道這部小說,是1999年10月的一個凌晨,在大學宿舍的樓道里。
每到凌晨,男生宿舍的樓道都是一個非常有野生氣息的地方。男生們拿出板凳和椅子,在樓道里看書、寫作業、讀英語,沒有智能手機,也沒有筆記本電腦。因為大一剛入學,大多數人沒有個人電腦,新生寢室也不聯網,上網都去主機房。離我們12號樓距離300米的清華大學主機房是當時教育部“主干網絡”所在地,當時全中國互聯網接入速度很快的地方。
那個夜里,5層的樓梯口有一個對門寢室的半長頭發少年,坐在椅子上看一本書,一會兒呵呵呵地笑,一會兒嘆氣,一會兒蹲到了地上,把書放在了椅子上,胳膊肘撐著椅子,椅子上還放著一摞信紙。
過了一會兒我再從寢室出來,發現他坐在椅子上,手里捧著那本書,眼神茫然地看著前面坑洼不平的水泥地,悵惘若失。一會兒他去水房了,書扣著放在椅子上,我湊過去看了一眼書脊:《第一次的親密接觸》,繁體字。
旁邊的信紙,是他預備給遠在南京讀書的女朋友寫信用的。此后的幾年,我見過他女朋友若干次,更見證了他們每周三封信的鴻雁傳書,直到無疾而終。

我跟這個人成了非常好的朋友。
他讀詩歌和小說,也寫詩,當時我也讀詩、讀小說,也寫詩和小說。但他懂電腦,高中的時候就自己做網頁,我們班的網頁就是他做的。后來我也跟著學會了做網頁,用的是一個叫frontpage的微軟Office自帶工具,我的網頁上放的都是自己的小說和詩,有新詩也有舊體詩,網頁掛在了Chinaren上,起了一個尤其陳腐的名字:松鶴齋。
我跟這個哥們經常混在一起,去學校舊圖書館的影像資料室看英文原版電影,騎著自行車出清華西門過馬路,到當時很破敗的北大小東門旁邊的“雕刻時光”酒吧,看定期播放的藝術電影,聽未名湖詩歌朗誦會。錢理群先生站在酒吧中間,一字一頓地讀著穆旦的《在嚴寒的臘月的夜里》,身邊都是年輕人,一片安靜,只有窸窸索索的呼吸聲,我感覺錢理群先生毛發稀疏的頭頂閃著光。
到了大三,他轉去了新成立的新聞傳播學院。我則忙于在校外接私活兒,我跟這哥們的聯系變少了。離開學校后,他一個懂技術的文科生,用他對當時很前沿的P2P技術的理解,參與創辦了一家曾經名噪一時的流媒體公司。接下來的8年,我們只見過兩次面。
再一次見面是在美國。那會兒我正好在硅谷工作,他當時在硅谷出差,為他創辦的一家用云技術做游戲和視頻點播的公司尋找當地合作伙伴。他去了我在Sunnyvale的公寓,我們一起去舊金山市區吃了頓飯,然后我去采訪Instagram。
剛從Instagram出來,手機收到消息:喬布斯去世。那是2021年10月6日。
我馬上趕往喬布斯在Palo Alto Waverley Street的家門口。路上他給我電話,說一起過去。等我們到了的時候,門口已經放滿了鮮花和蠟燭,人們簇擁在四面,祈禱和低語。我們想打印一張喬布斯的遺照,但傍晚打印店都關門了。這個時候他拿出了自己的iPad,下載了一張喬布斯那張聞名的黑白遺照,全屏顯示,把它放到了喬布斯家門口的地上。
身邊的人們低聲說:“Wow good idea”。那個iPad,后來被留在了那里。
在那之后,我們又很少見面。我創辦了PingWest品玩之后,有一次和他還有他正大著肚子的老婆一起在后海擼串,聊融資的事。再之后偶然在酒店大堂碰到了,寒暄幾句,大家都很忙,都有一堆糟心事。
很近兩年,他又開始了新的創業項目:做區塊鏈和代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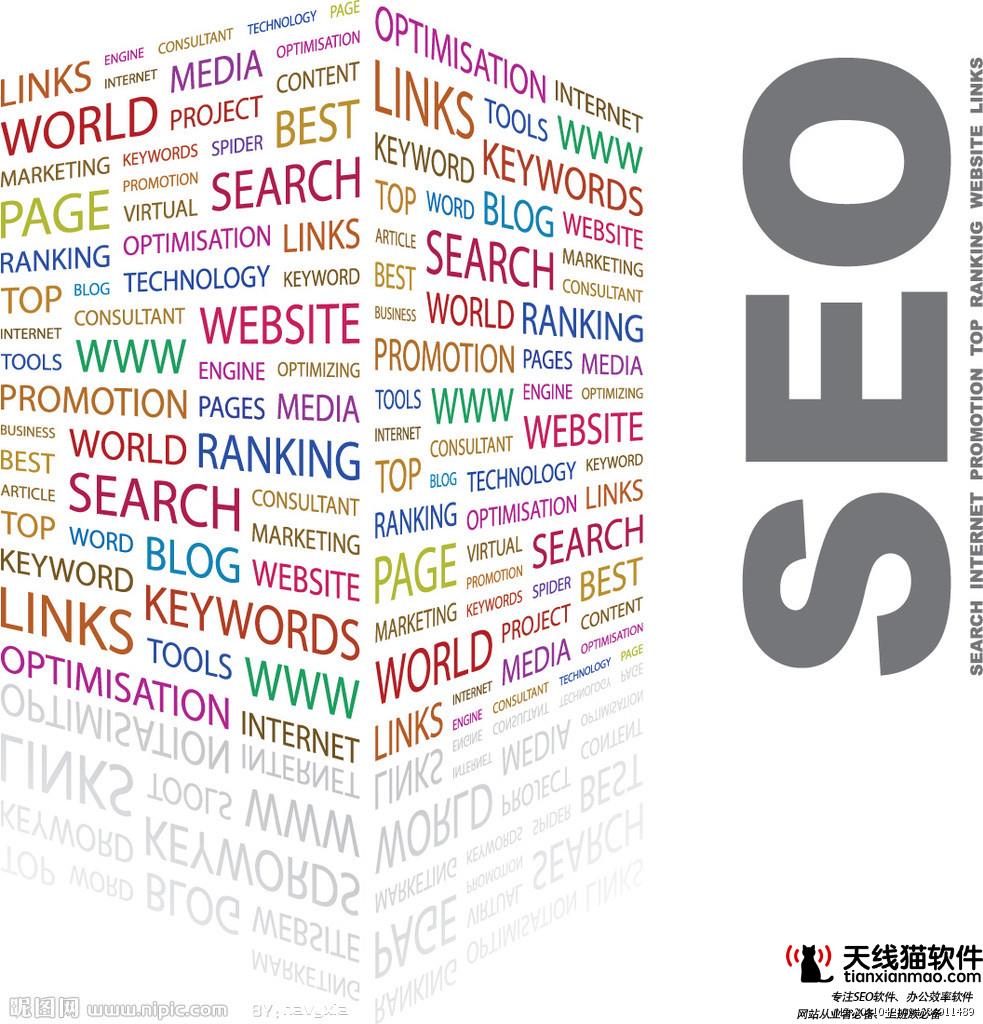
前不久PingWest品玩發布了一篇很爆炸的調查報道《莊家杜均》,講了點區塊鏈和代幣市場背后莊家操縱信息、交易和價格的內幕故事。做區塊鏈的人看了褒貶不一,當事人自然更五味雜陳。其中一位當事人發了條朋友圈,“澄清”和撇清了一些事,并表達了對我和PingWest品玩的憤怒,一些幣圈人物在下面點贊。
在點贊的人里,我看到了他,這個第一次讓我知道《第一次親密接觸》、熟悉了快20年,現在人在幣圈的朋友。
但我相信,我們還是朋友。
第一次網聊
我第一次上網是在1998年,到現在也整整20年了。
在我表哥的家里,伴隨著電話撥號接入的雜音,打開了“263信息港”的網頁,整個網頁加載下來花了差不多5分鐘,我記得那5分鐘的時間,我的眼睛一直盯著屏幕,比我后來創辦公司第一次打開自己媒體網站的那一刻還激動。
接著傳來了我大姑的敲門聲:“怎么還在網上呢?我要打電話都打不了!這月電話費又得300多!”。
但我的第一次真正“網聊”,確實是受《第一次親密接觸》影響。
1999年10月,在263聊天室,在半分鐘滾動一屏的密密麻麻聊天室里,我問了一句“有在清華五道口四面的網友嗎”?很快收到了10多條消息。那個時候北京的互聯網用戶,似乎差不多都在五道口四面。
很快,我跟一個隔壁學校圖書館學專業比我大一級的女生聊了起來。雙方基本把對方的底細都問遍了。哪里人、年齡、從哪兒考過來的,平時讀什么書,看什么電影,有什么愛好,有男朋友女朋友嘛……什么都聊了,就是沒聊身高體重三圍,那會兒在聊天室,似乎不太興聊這個。
當時的263聊天室還很簡陋,我記得連開小窗的功能都沒有。假如跟一個人私聊,只會在聊天刷屏的界面里用加粗的方式標記出來,加上一個@的標識,一不小心就錯過了。下次再想跟她聊,得先看她在不在聊天室的人列表里,假如碰巧在的話,點她的名字再開聊。其實很好的方式是約好了下次上網聊天的時間,跟線下約會也沒什么兩樣兒。可是就是這樣兒,在兩個學校相隔幾公里遠的兩個機房,我們居然聊了兩周多。
兩周多之后,我們開始通書信。網聊再怎么深入靈魂,還是不靠譜,還是沒寫信好,這是當時我們的感覺。在通信中,我們互相告訴了對方自己的真實名字,其實網上已經聊得透透的了,但就是名字這一關,打死也不說。那會兒流行的說法是在網上沒人知道你是一條狗,狗哪兒來的真實身份呢。
那個女生有一個非常男子氣概的名字。然后我們就見面了,好一個義薄云天的女青年。
故事就這么結束了。
又過了一年,聊天室變得多了,成了各大網站的標配,也開始變得細分了起來。在ChinaRen的一個細分主題聊天室,我第一次找到了one night stand的對象。
那是在清華南門馬路對面一片很破的小旅館里發生的,里面住滿了全國各地來北京上新東方和考研班的學生難民。房間35元一晚,有那種裝著膽的熱水瓶。
平心而論那是極其乏善可陳的一個晚上,連照片也沒換,就發生了。但我還是很興奮,第一次在網上搞成了這種事,人生成就get,似乎征服了什么東西,那種快樂和刺激的感覺,后來的陌陌和探探們從來也沒給我帶來過。
幾乎是在那同時,我開始用QQ了。那會兒叫OICQ,我的第一個OICQ號是六位數。我還用過ICQ,有著一個像大王花一樣的logo。但不知道為什么,我還是更喜歡聊天室。可能跟我的OICQ上一開始加的就全是同學有關系。當時我負責收古代詩歌課的期末論文,把一個同學的論文搞丟了,她找我算賬就是在OICQ上算的,我怎么可能喜歡這個東西。
在我們那個據說平均智商很高的學校,尤其是理工科的學生里,ICQ和OICQ一出來就有了跟進模擬的人。大一的時候跟我同宿舍的一個工程物理系的浙江諸暨人,很快就搞出了一個叫OICU(oh I see you)的東西。現在來看,那是一個基于校園為單位的OICQ,當時似乎也有不少人在用。那會兒學校南門主路上也一天到晚掛著“第二屆大學生創業大賽”的紅底黃字橫幅,很多宿舍樓的機房服務器上都放著幾個學生做的項目,但似乎沒什么人是沖著參賽融資去的,基本都在玩票。
另一個大一跟我們同宿舍的工程物理系的哥們提到那個做“OICU”的哥們的時候羨慕地說:“他要出去打工,一個月肯定能掙8000!”8000塊,一個當時大學畢業生的天價薪資。
大二搬了宿舍之后,我跟那個工程物理系的“OICU”發明者再也沒聊過天。再“碰到”他是在一個北加州校友微信群里,我順著他微信綁定的LinkedIn賬號,大致了解了他后來的走向:留校讀完碩士去德國拿下了計算機博士學位,參加了博士后項目,然后去紐約的斯隆-凱特琳癌癥中心做大數據診療癌癥的研究,然后來了硅谷,在一家高級AI新興公司做數據科學家,接著帶領商業化團隊。
He deserves it。
但我沒有加他的微信,只是想起了那個叫“OICU”的早期聊天軟件。
第一次用Google

那是2000年9月,我們剛搬了宿舍。大二的宿舍可以連網了,我們也有了自己的電腦。
我第一次在宿舍里看到了一個打開的網頁,上面是六個顏色不同的字母:“G-o-o-l-e”,下面是長方形的框。
用過搜狐的我猜測它應該是一個搜索工具,但我之前從來沒見過也沒聽說過這個網站。打開這個網頁的是我們宿舍很洋氣的一個哥們,他的英語和法語都接近母語水平,平時下載各種法語和小語種的音樂聽,而且從那時候起他就是一個多元文化的推崇者,覺得英語和美國流行文化太“沙文主義”了。所以當我問他這個搜索網站叫什么的時候,他跟我說:“Guu-gu-le”,Google的法語發音。
在之后的幾個月,我一直管這個我剛熟悉的搜索網站叫“Guu-gu-le”,直到有一次被旁人糾正:什么Guu-gu-le,它叫“Gu-gou!”
好吧,甭管它叫什么,反正從那會兒起我就是它的用戶了,搜狐的搜索框很快被我扔到了一邊。此后的18年,我一直是Google的用戶,無論在它能非常順暢的訪問的時候,還是在它經常不能順暢訪問的時候,再到它幾乎不能順暢訪問的時候,我一直是它的用戶。
一開始用Google的時候還很小心翼翼,因為服務器在美國——宿舍連網免費,但訪問海外網站要按流量計費,從學生賬戶充值里扣,我記不清多少錢了,可能上一個鐘頭一天食堂的菜錢就沒了,反正很貴。那時候阻礙我們訪問境外網站的,不是看不見的墻,而是因為太貴。
用Google也沒什么尤其的感覺,搜資料搜新聞挺方便的而已。那會兒百度也出來了,我也經常用。坦白說,我當時不覺得兩者有什么區別。直到2003年冬天的一個晚上,我看到了《大眾軟件》雜志上的一篇文章,專門講Google。講它從斯坦福的緣起;講它希望讓用戶盡可能短地停留在自己頁面上的理念;講它80:20賦予員工創造力和自由度的企業文化,講它的員工有免費食堂,上班可以帶寵物;講它“不作惡”(Don't be evil)的信條……
可能是當時是簡單被洗腦的熱血青年,讀完《大眾軟件》上的那篇文章我就跟自己說:我要永遠做Google的用戶。
2004年秋天,Google推出了Gmail,我是第一批用戶;我可能也是國內很早用Google Earth的一撥人之一。2005年Google聘用了李開復擔任大中華區負責人并讓他吃了微軟的官司,當時我切齒地痛恨微軟和鮑爾默。那會兒我還在公關公司上班,想過“該怎么加入Google”的問題,但我居然從來沒為這件事努力過。
2006年我成為了一名報道科技的商業雜志記者,逐漸開始有了接觸Google的機會。2007年Google跟搜狗輸入法鬧出“抄襲詞庫”風波的時候,我在報道里幾乎不加掩飾地站在了Google的一邊。現在看,這么做可能不是一個合格的記者該有的姿態。以至于后來我在《第一財經周刊》的領導伊險峰動過禁止我報道Google的念頭:“你丫整個一個它的信徒,怎么做好它的報道?!”
但必須得說,因為有了借職務之便一線接觸Google的機會,我趕上了近距離觀察Google、報道Google和體驗Google很美好的時光。
2008年,Google開始發力云計算,跟清華大學合作給計算機系的學生開設“小學期”的云計算項目必修課,計入學生學分。我參與了報道這件事,第一次接觸了什么是云計算,而且是直接從Google的研發經理那里知道了什么叫云計算。2008年9月,Google發布了Chrome瀏覽器,我當時就蹦了起來:“這是一個能把微軟徹底干趴下的網絡操作系統!”。接著在一個北京時間的凌晨,我電話里采訪到了當時負責Chrome的工程總監桑達 皮恰伊(Sundar Pichai),現在的Google CEO。
說來也是厲害,當時為一款Google在全球發布的產品,一個請求就能采訪到它的全球項目負責人,真的是我的記者生涯里一段相當美好的經歷了。
然而彩云易散,事情很快起了變化。2009年,Google在中國的運營碰到了越來越多的問題。2021年1月10日,Google在中國的策略發生了重要調整,即所謂的“退出中國”風波,3月26日,靴子落地了。
那段時間,我去Google中國的門口“非法獻花”過,集體簽名過。還把我做的一切發上了微博,被刪了繼續發;再被刪發開心網,然后被刪得更快。我貼著支持Google的一個胸簽出現在辦公室,被領導命令不許參與這件事Google的報道,我氣沖沖地坐在座位上刷Google的相關新聞,竟然在辦公室里哭了起來。
現在想起來,我當時確實缺乏另一個維度的思考:比如作為一家商業化運營的公司,Google有沒有考慮過我——一個普通的Google在中國的用戶面對這件事的時候,會受到哪些切實的影響和利益損害?再比如對Google在中國的幾百名員工,他們的處境、去向和現實利益,會不會受到損害?現在看來,Google當時對這些事的思考,確實很少。當然我意識到這些問題,差不多已經是2021年之后的事了。
至少那段時間,2021年1月-3月Google在中國的命運迎來重要拐點的時刻,真的也是我整個人精神世界的“至暗時刻”。
之后,我經歷并見證了Google在中國的一個又一個挫折晦暗的節點。直到這兩年,Google在中國重新找到了它能做的事和做事的方法,我也一并見證過。這幾年我一直都參加Google I/O 開發者大會,這幾乎是我要求自己每年必去的優選的全球的科技活動。從AlhpaGo到TensorFlow,我仍然想見證、經歷、感受、呈現和記錄這一切。
因為究竟,這是陪伴我整個互聯網生涯時間很長的一家公司。從2000年到現在,整整18年了。下一個18年、36年和54年,我仍然需要它。
第一次網購
說實話,我第一次經歷的網購并不是什么真正的網購,而是給我普及“Google”的那個室友自己的小生意。作為一個很洋氣的,熟練把握法語,并精通德語西班牙語芬蘭語捷克語的語言天才,他也是一個藝術和音樂愛好者。2001年左右的時候,他天天在電腦上搗鼓著從全球各地下載一些偏門的多語種流行音樂,然后刻成光盤,自己設計封面和附帶中文翻譯的歌詞單(當然都是自己翻譯的),裝幀精美之后,掛在自己的主頁上對外賣。
別的人我都記不清了,我就記得一個叫Lara Fabian的能同時用法語、西班牙語和意大利語演唱的比利時女歌手是他的很愛。他為她做了很多張光盤。有的時候一個月居然能賣200-300塊錢,當然刻光盤和打印裝幀之類的,估計起碼也得花100多吧。另一點很牛B的是,這哥們當時就開始用PayPal收款了。
可他的用戶是哪兒來的呢?那些人又怎么肯先打錢,不怕他收了錢不交貨呢?我不清楚。可見那個時候而的用戶獲取和信任機制邏輯,跟現在是徹底不一樣的。很草莽,但也很有趣。
我自己第一次網購也是在2001年底,那次我媽讓我請幾個關系好的同學周末來家里吃飯,我第一次用那個叫“e國”的網站,訂購了幾桶大可樂。
在這家域名后來被1萬多人民幣賤賣的電商網站的網購經歷我記得是這樣的:打開網站——搜索可樂——填寫配送地址——留電話(當時還有家里座機的選項)——等著送貨上門。付款?當然是貨到給現金了,當時哪兒有網絡支付工具。據說e國當時在北京有500多名穿著紅色馬甲的配送員,這在當時的互聯網界是個大新聞。現在來看,他們可能是很早的一批餓了么“騎士”。
誘導我去用“e國”第一次網購的原因是當時e國搞的“e國一小時”活動——北京四環以內,任何東西下單,一小時之內送達。這在現在看都是很厲害的配送效率。不過想想看,恐怕當時一個配送員一天也送不了幾單,一個小時當然能送到了。不過,在我用它訂可樂的那會兒,已經有必須滿20元才送貨的限制了。我也是后來看keso的文章才知道,當時真有人只下單了一罐百事可樂然后讓人家一個小時送來且送到的事發生,估計e國是被這種人坑苦了。那個只讓人家送一罐可樂的人叫姚勁波。
但我要講的是,我訂的幾桶大可樂,一小時內并沒有被e國送到。兩小時也沒送到,三小時也沒送到。其實,它根本就沒被送到。
那你能怎么辦呢?追蹤物流情況?沒這個查詢系統。聯系騎手?騎手沒有手機。聯系客服?經常占線。總之,我第一次用e國網購的體驗就是——網購失敗了。它不是送晚了,而是就沒送到。幸虧當時不能預先付款,否則當時幾十塊對我來說也是筆大額消費。
為什么沒送到呢?不清楚。后來也是我成了一名互聯網記者,考據史前中國互聯網資料的時候才知道,當時e國的經營已經四面楚歌了。一家公司每年也就收入幾百萬,做一單虧一單,沒法解決物流信任和支付信任的公司,只有等死的份。
這件事當時對我沒什么影響。倒是我媽嘟嘟囔囔地下樓買可樂去了。一邊穿衣服還一邊嘮叨:“就跟你說了別讓你網上買,不靠譜,非買,我菜都做好了還沒到,還得我去買去,一會兒要是送過來了跟他說不要了啊”。
現在呢?我媽經常去我辦公室掃蕩,看有沒有被我不小心扔在那兒的京東和盒馬先生優惠卡,然后都揣包里帶走。連家具都不出門買了,平時收的包裹比我還多。
我真正大規模使用網購是在2021年之后了。2020年春節前我帶著公司團隊去胡志明市考察,參觀了一家叫Tiki的公司,創始人被稱為“越南的劉強東”,做電商,以賣書為主。我問支付用什么工具,他跟我說了一個我現在不太記得住的支付工具的名字,又補充了一句:當然我們也支持貨到現金支付。我馬上找補了一個問題:網絡支付和貨到付款的比重大概是多少?創始人猶豫了一下,跟我說:大概一半一半。
我覺得“一半一半”可能是一個有點被修飾過的數據了。我沒有繼續往下問,但想起了2001年那次在“e國”上想買幾桶可樂而不得的事兒。在那次網購之后,我很久都沒網購過,留下了心靈陰影,我也跟很多人說過e國是一個多不靠譜的網站,直到前幾年了我還跟別人這么說。
現在來看,我們真的有必要對作為先驅的“e國”表達一下由衷的敬意,坑都是被這樣的先烈踩到并且填平的。當然我們也得感謝一下當時在“e國”上只下單一罐百事可樂,并且一個小時內收到了的姚勁波先生。估計這件事對后來的“58同城”,多少有點幫助和啟迪。
我還是偶然會懷念一下那個下了單收不到貨也不用付錢的電商原始社會。
第一次網絡論戰
我第一次參加網絡論戰,是2001年的夏天,在一個叫“黑板報”的左翼論壇。
很明顯,我是過去砸場子的。那會兒已經自詡“自由主義者”的我,在“黑板報”上給自己起了一個現在看上去傻X到不能再傻X的網名:“hollyright”(神圣右派)。很顯然,上這個論壇,就是去拍左派的磚,跟他們死磕沒完的。
“黑板報”是以音樂和話劇出品人張廣天為精神領袖的一個BBS論壇。在1990年代末和本世紀初“先鋒戲劇”在中國嶄露頭角的時候,張廣天給孟京輝的很多先鋒話劇都配過音樂做過曲。其實他本人也是一個“先鋒戲劇”實踐者,只不過他的先鋒戲劇走的是活報劇的路數,而且有鮮明的意識形態色彩——左翼。
1990年代末和本世紀初是一個左翼思潮重新興起的歲月。張廣天的先鋒話劇《切 格瓦拉》和《魯迅先生》都有點這種借圣壇上的革命人物或左翼文化領袖為現實獻祭的意味,主張尋找革命理想的崇高,批判物質消費與西方文化,質疑資本和階層分化等等。不過當時血氣方剛以“自由主義右派”自居,相信人權高于一切、市場大于一切、資本必定通往自由和光明的我,是斷斷看不慣這些,要殺過去辯個水落石出的。
當時正值張廣天的話劇《魯迅先生》在北京青藝上演。我看完了之后寫了一篇《魯迅的還魂和變態》,痛斥這部劇借魯迅的名還極左的魂。文章里用了大量剛剛學來的“拼貼”、“戲仿”、“遮蔽”和“解構”之類的新左派文藝批評名詞。這篇文章在我貼在“黑板報”之前已經發表過了。我貼在以張廣天為精神領袖的大本營“黑板報”上,無非是想逞一下類似朝革命領袖畫像上潑墨的那種快感。
這一板磚炸出了不少潛水的“右派分子”,也有很多黑板報左翼路線的維護者反駁我,我就跳出來一一論戰。當時在BBS上論戰的一個好處是:盡管論爭少不了意氣用事和口舌之端,也少不了誅心之語,但每個人多少都說出個一二三四來,用臟字罵人也有個說臟字的章法。總之,那些日子我一睜眼就論戰,那個月電話撥號網費花了600多。
很快我的這個帖子被“黑板報”的版主王佩給駁了,駁得我有點不知道該怎么懟回去。因為他的邏輯和引用能力都比我強大N圈,尤其是我用來在文章里套用的那些新左派文藝名詞兒,他很簡單就看出來我在怎么偷用和盜用。這件事給當時的我刺激很大的是,當時不知道天高地厚的我第一次知道:原來左派也是讀書的啊,而且還讀得很透。
當時我還不知道原本這個“黑板報”原本還有王小山的一份兒,早在我上去砸場子之前,王小山就已經因為價值觀不同跟王佩散伙了,去別的地方玩了。很快我又找到了西祠胡同,在那兒落了個腳。起了另一個今天聽起來更肉麻的名字:“拯救與逍遙”。
這個地方我喜歡,因為他很“右”。
當年的互聯網論壇就是這個樣子的。平臺很多很碎,這個地兒三觀不合了鬧掰了,換個地盤兒扯面大旗重新來過。至少當時的互聯網BBS,還能分個左和右。
剛到西祠玩就趕上了“911”事件,上面的“銳思評論”板塊天天吵得不可開交。有美人希右派、有中國民族主義右派、有新左派,也有中華田園的革命左派,天天混戰,一輪接著一輪。只要不罵祖宗八輩兒,沒人管,也沒人刪貼。當時的銳思評論版主既標榜自己是基督徒又是自由主義者,被另一個自稱右派又同時反美、還以正宗基督徒自居的ID“藍牙吸血鬼”咬著不放死打,但他從來沒被刪過貼。這個被罵得底兒朝天又幾乎不刪貼的“銳思評論”版主,叫安替。
我在“銳思評論”第一次被安替置頂的帖子,是一篇紀念辛亥革命90周年的文章。現在來看,那篇文章暴露了一個初階民國粉種種幼稚之處。但就這么一篇公開盛贊民國甚至懷念民國的文章,能被置頂,能一直活著,直到西祠胡同作為一個網站整體關門的那一天。現在想起來已經是很值得回味的事兒了。
在西祠胡同我經常去的另一個板塊是“王小波門下走狗聯盟”,里面布滿了“向王小波致敬”的戲仿作品,大多都筆觸粗糙,形散神不似,但每個人都能寫出那么點兒東西來。還有不少關于王小波的評論,以及各式民間自發研討會的發言記錄整理。差不多在那之后,我在中文互聯網世界就再也找不到一個能聚氣來那么高人氣討論王小波的地方了。
我第一次見“王小波門下走狗聯盟”的版主“歡樂宋”,是2001年的夏天。我和一個朋友約了當時還在人大讀研究生的歡樂宋在人大西門的一家火鍋店吃飯。那天我們扯了很多淡,關于王小波,關于文學,關于政治和其它。到很后,歡樂宋一臉歉意地跟我說:“對不住哥們,你來人大找我吃飯,按理說得我請客的,可到了月底手頭兒實在是緊,兜里只有50多塊錢了,這頓你能不能先替我付了,下次我一定請。”
于是,一個在讀本科生請一個在讀研究生吃了頓火鍋,花了50塊錢。
我第二次見到歡樂宋,是第二年春天,在萬圣書園王小波逝世五周年的研討會上。那天我見到了歡樂宋請來的發言嘉賓、“銳思評論”版主、聞名新聞人安替。
那天大家聊得很多,聊完四散而去,再分頭聚會。很多事記不清了,只記得隱約聊到過王小波在一個敏感歷史事件發生前后的心理狀態。以及當安替在發言環節大罵李銀河沒有照顧好王小波的時候,下面的噓聲;還有安替說自己是虔誠基督徒,但贊成同性戀的時候,遭到了一個“正統基督徒”站起來的當頭棒喝,兩個人對壘了10分鐘。
那時的萬圣書園,這樣的場景很常見,歷歷在目。
王小波逝世10周年在魯迅文學館的研討會和展覽會上,我又見到了安替和歡樂宋。當時西祠胡同每況愈下,大家的陣地很快就維持不住了。
再后來,微博誕生。2021-2021年,我在微博當了三年“戰士”和“中V”。2021年之后,微博已經沒有我說話的地方了。每一開口,必被問候全家、必被人肉,從王寶強粉絲到賈躍亭擁躉,不一而足。從互聯網上人人會寫文章,到互聯網上人人會罵三字經,看上去變化也就是在兩三年的時間發生的。
西祠胡同上我熟悉的兩個版主。“銳思評論”的安替,在一系列被陸續關停和封禁的媒體供職過,很后創辦了國際新聞平臺“創業說”,成了一名創業者,同時成一枚忠實的米粉。很近我們見面,他很關心的是用AI和機器翻譯,如何更高效率的生產新聞,這已經很張一鳴了。
而“王小波門下走狗”的歡樂宋,在2007年王小波逝世10周年的研討會之后,就再也沒見過。直到三年后在《中國青年報》的頭版和評論版上看到他的本名,評論當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大義凜然,義正詞嚴,緊跟時代的步伐,每一篇報道都光榮正確,每一篇評論都鏗鏘有力。
我想起了那頓人大西門50塊錢的火鍋,以及“王小波”這個曾經把我們召喚到一起的名字。
作者:駱軼航
文章地址:http://www.meyanliao.com/article/online/547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