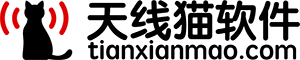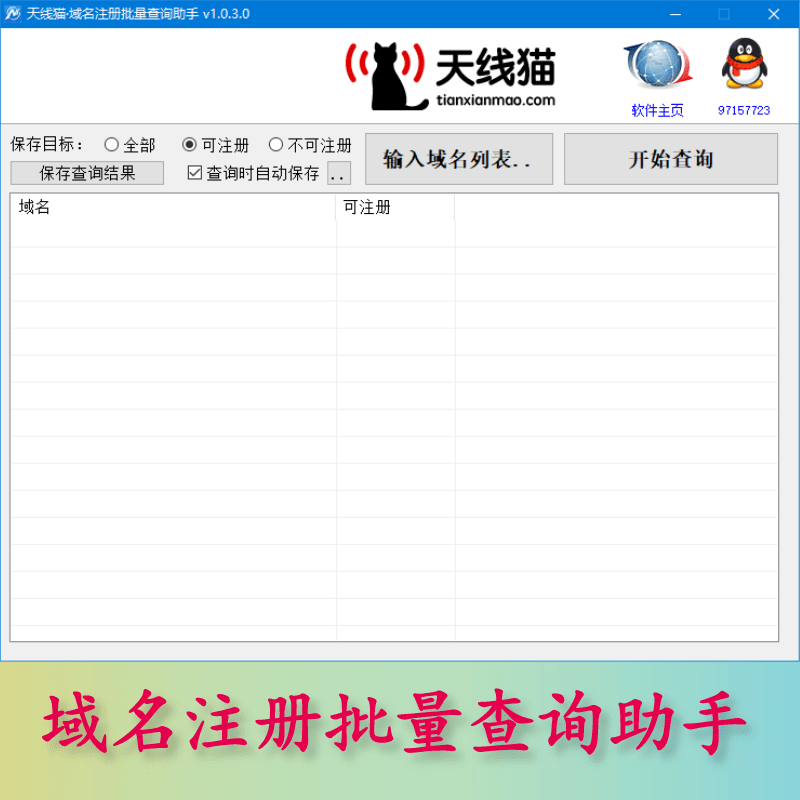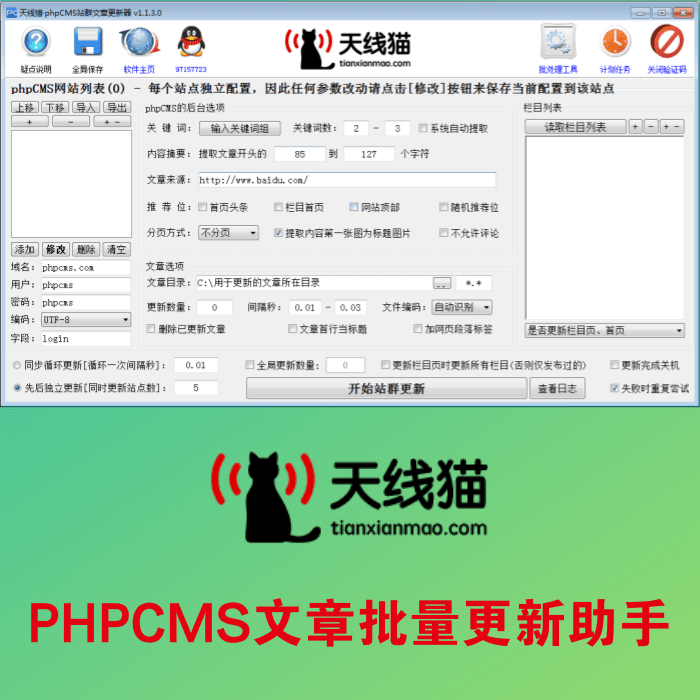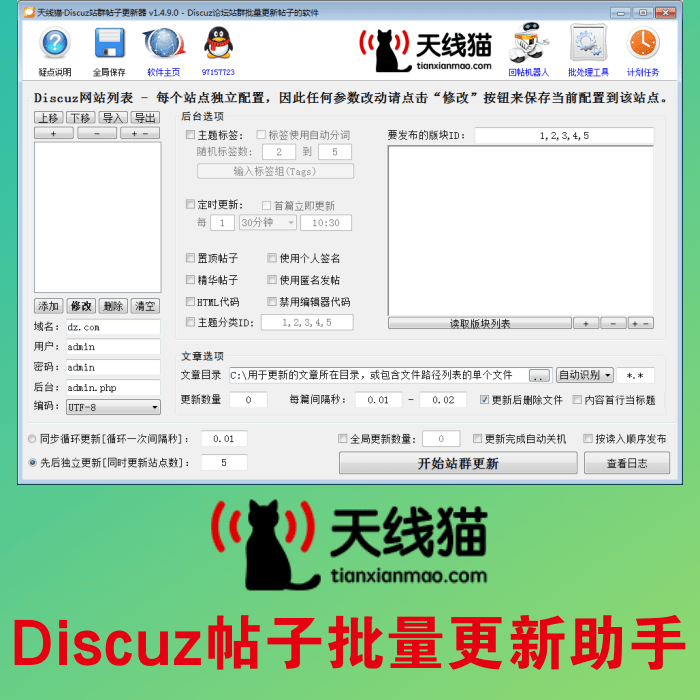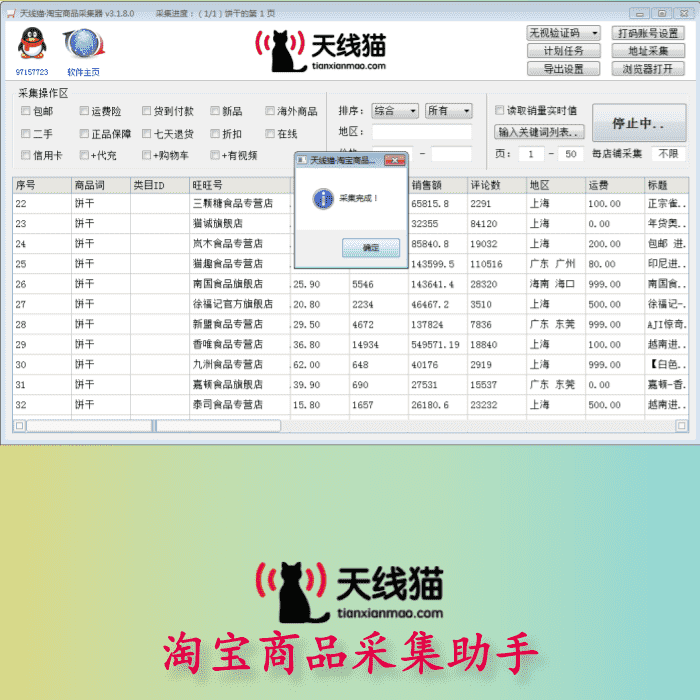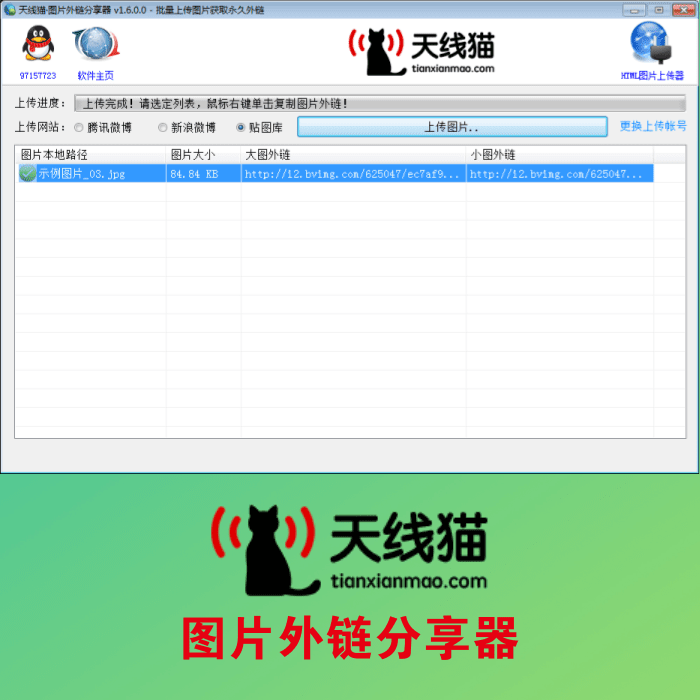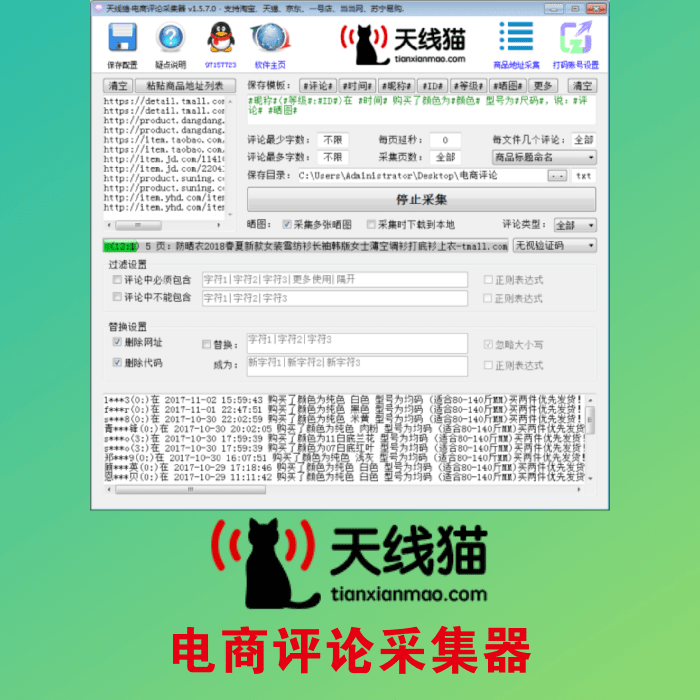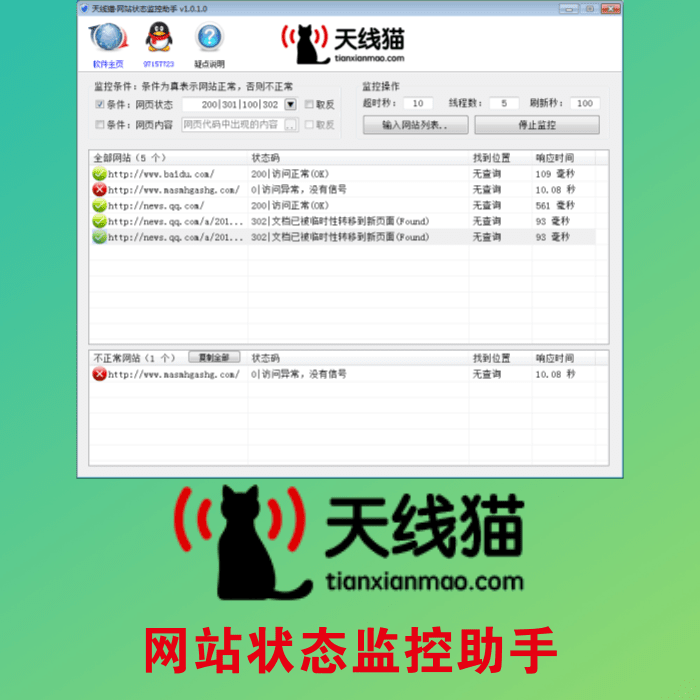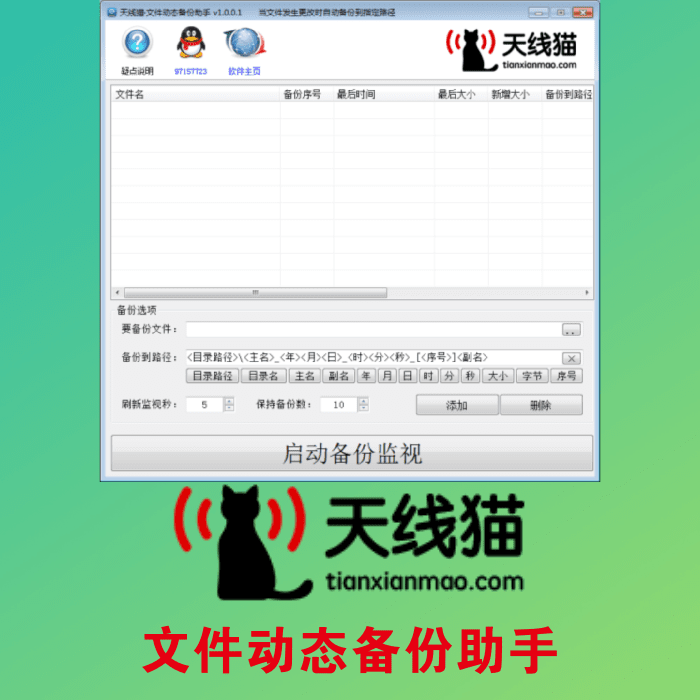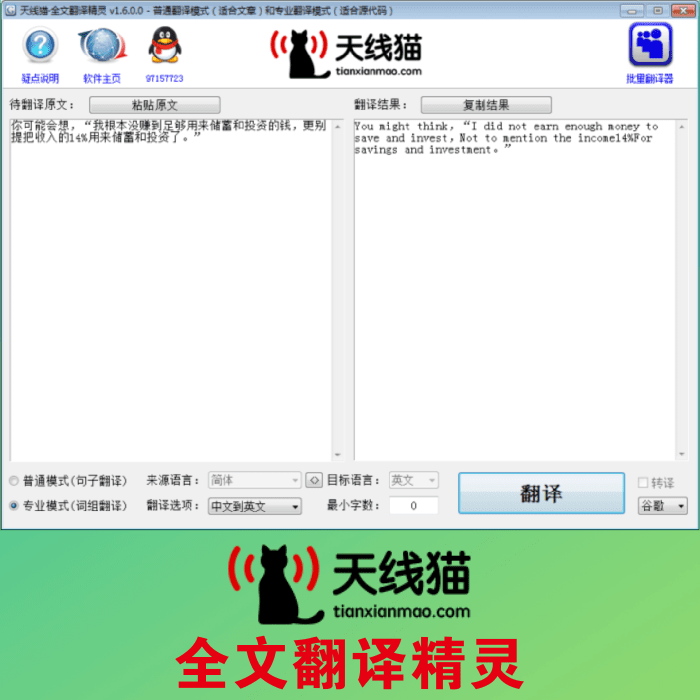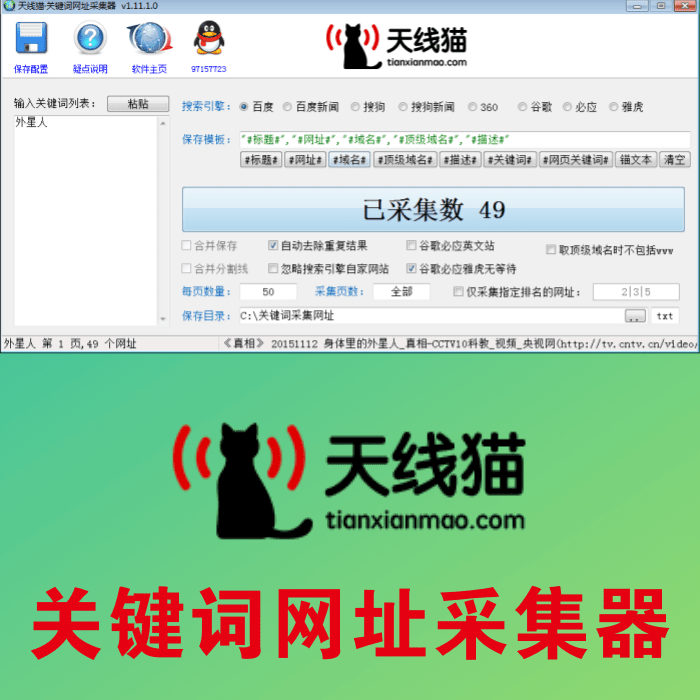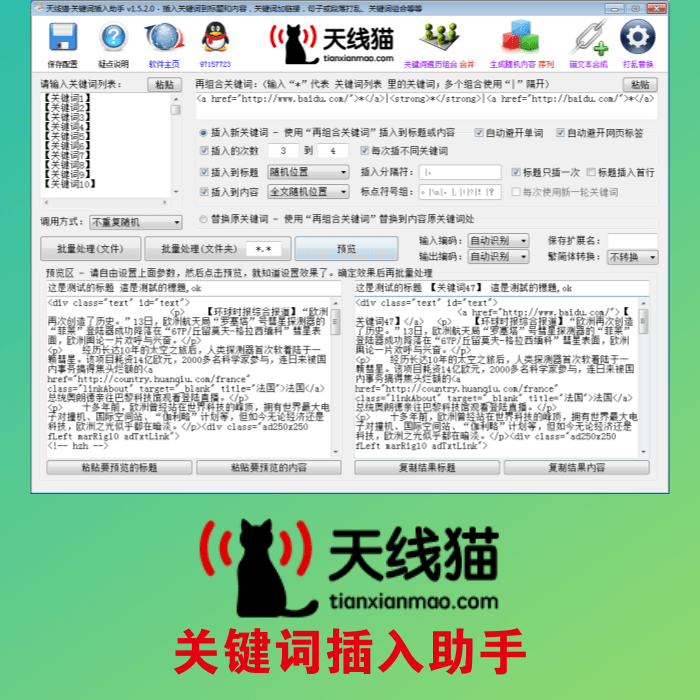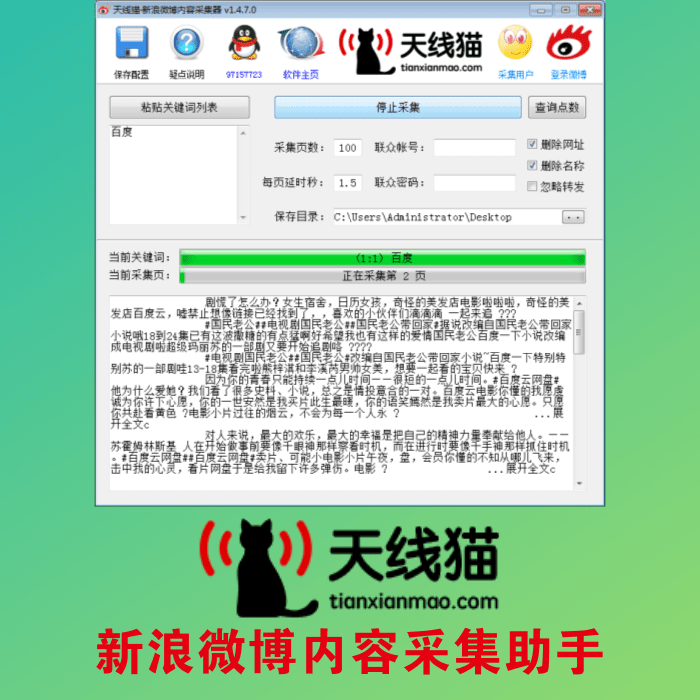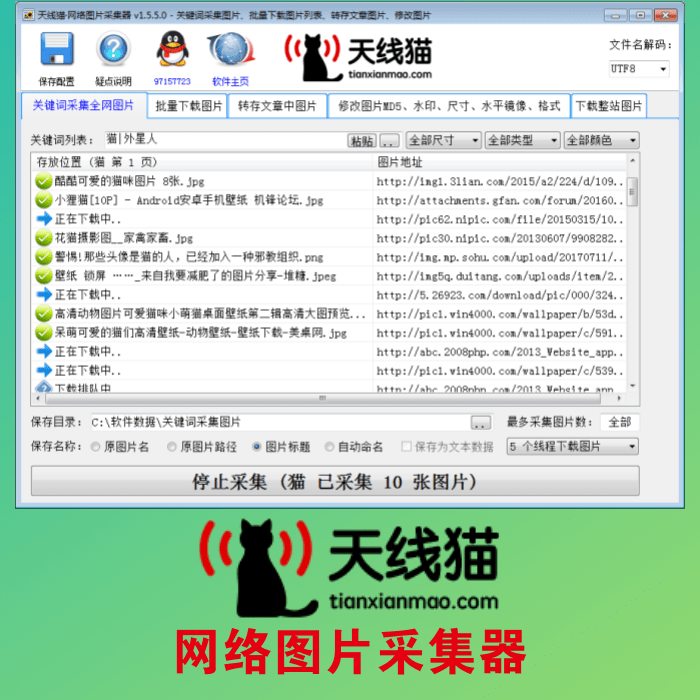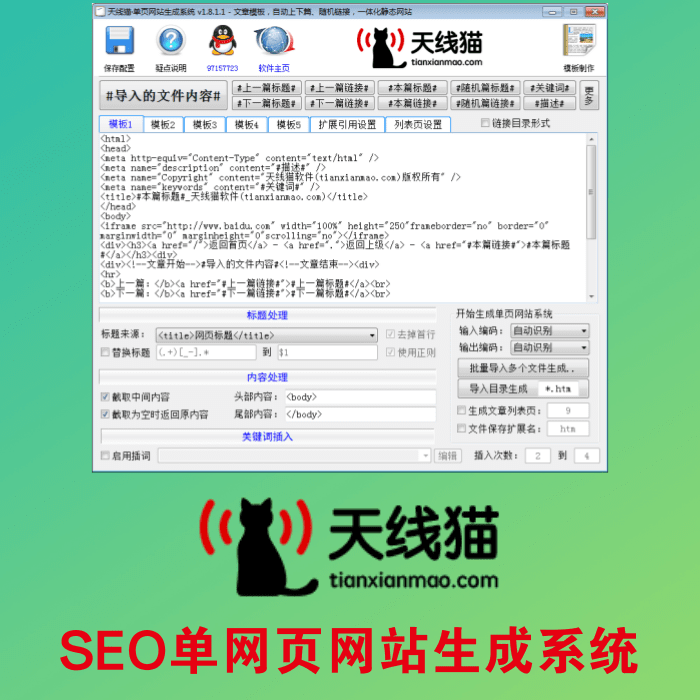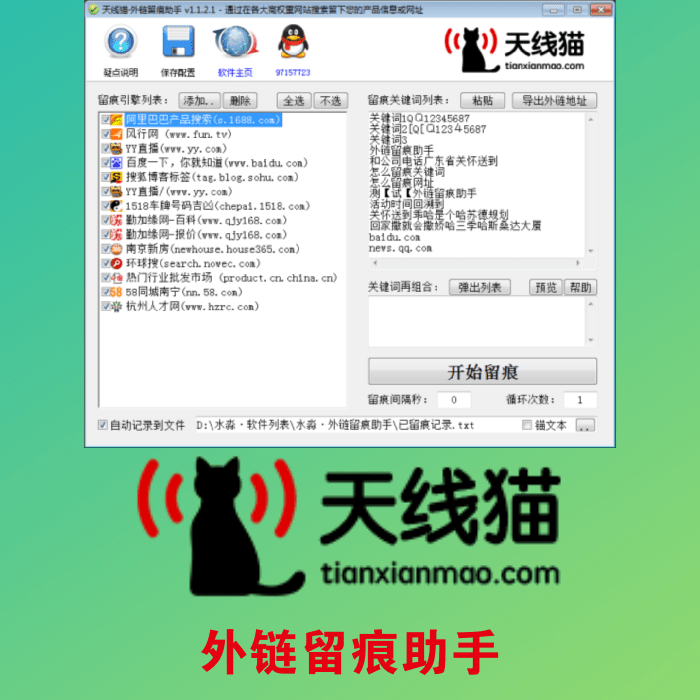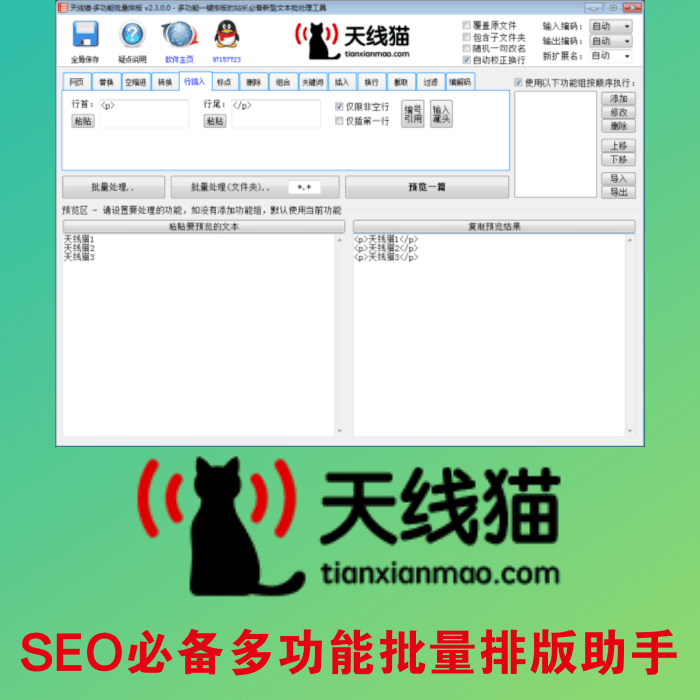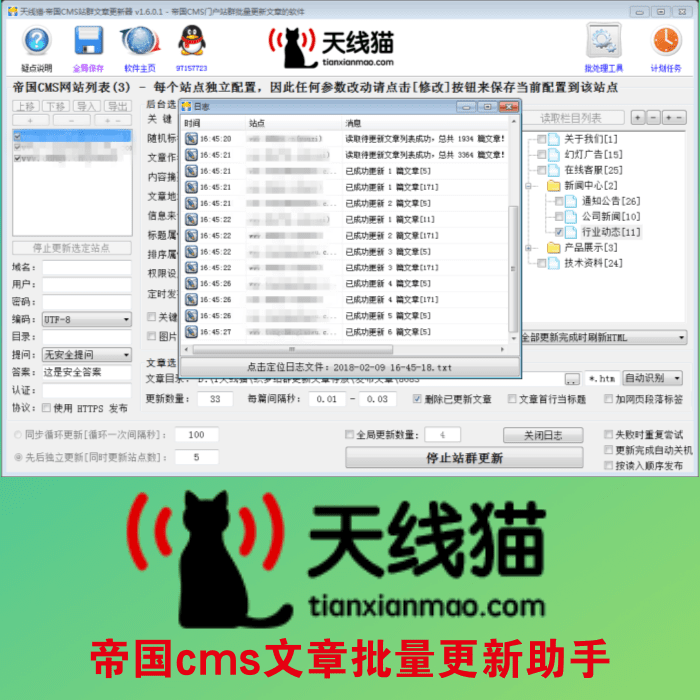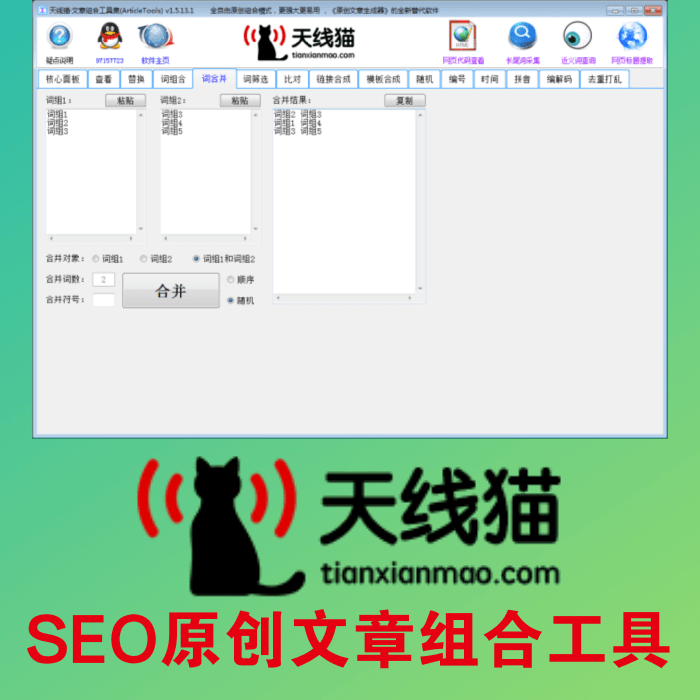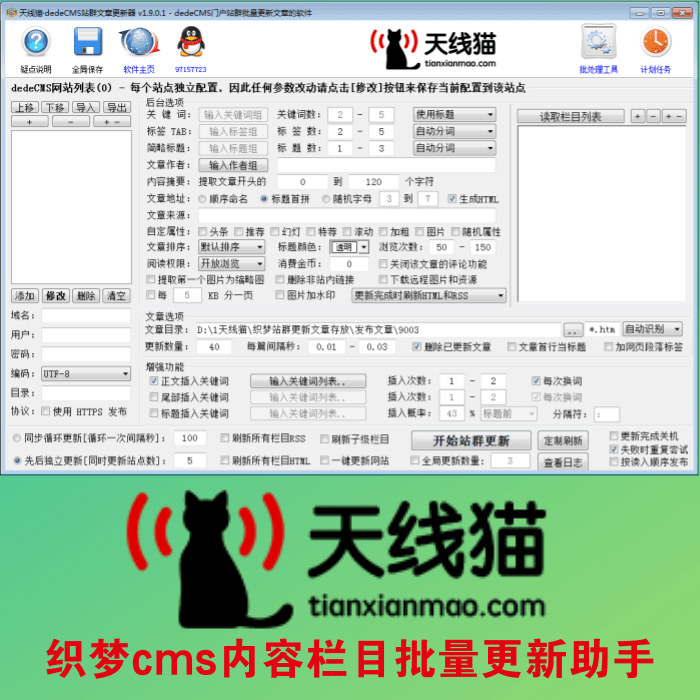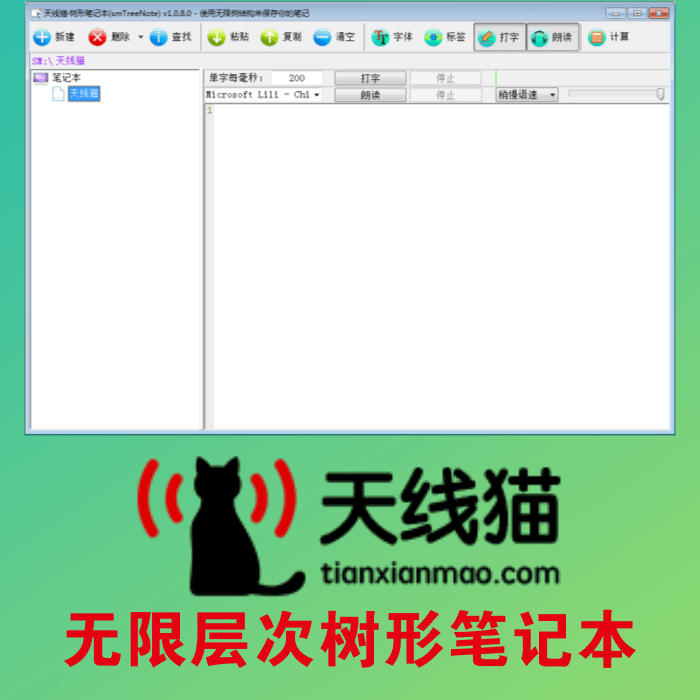馬東可能是 60 后里很懂 90 后、 00 后的大叔,他一直以此自詡。這也是為什么《奇葩說》從誕生之初,就能讓這一代互聯網原住民產生認同感并形成“代際”優越感的原因。

第一季《奇葩說》,每期節目開頭動畫中都會強調:“四十歲以上人士,請在 90 后伴隨下不雅觀看”。這種抖機靈式的自我調侃決定了節目初期定位。“ 90 后馬東”率領團隊,試圖突破上一代人的沉悶枯燥,表達新一代年輕人存在感和話語權的心理訴求,而后聚攏起一批對“奇葩”概念有尤其認知的文化娛樂消費群體。
“奇葩”一詞,經歷了至少兩個回合的基因突變。奇葩本意是指奇異而斑斕的花朵,常用來形容差別平常的優秀文藝作品或者出眾的人物,是作為教科書里的褒義詞出現的。第一天線貓SEO軟件微小變異,讓它成為了“不落世俗、有個性”的代名詞。現在,它更多是對異類的諷刺用語,這個語義雖然還沒被詞典收錄,但早已在網絡環境中被廣泛使用。
《奇葩說》讓奇葩一詞再天線貓SEO軟件變異,它開始成為包容多元不雅觀點的一種“消費符號”。社會的快速發展使得各個領域和圈層關系呈現出巨大代溝和溝通無能,碎片化的社交網絡切割了中國年輕人的生活,他們看起來并沒有因為享受到紅利而愉悅,反而焦慮層出不窮,而年長一輩的人們因為越來越不懂年輕人而焦慮。
既然是植根于中國的文化配景與社會結構,,隨著社會變遷,“職場關系”、“伙伴關系”、“男女關系”、“家庭關系”等也都發生了漸變。在人情社會中,這些變革,不管是外力因素還是內在因素,都離不開“情”字——親情、戀愛、友情等情感的羈絆。
但這樣的總結不免難免簡單粗暴。對中國式關系的經典概括是費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論,它原本是用來描述鄉土社會的概念,“我們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似乎是把一塊石頭丟在水面上所發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紋。每個人都是他社會影響所推出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紋所推及的就發生聯系。每一個人在某一時間某一個地點所動用的圈子是不必然相同的。”
雖然已經包羅了血緣親屬關系、地緣關系等,但說實話,費孝通的這個理論也挺模糊的。也正是因為這種模糊,恰恰說明了學者的嚴謹和克制,以及中國式關系的復雜多變。
就像《奇葩說》,辯論了四季,近百個辯題,除了少數腦洞題以外,大多其實都是圍繞各類情感,圍繞“中國式關系”展開的。在堅守底線基礎上,節目有價值傾向,但從沒有尺度答案。
陪同奇葩這個詞的意義迭代,《奇葩說》自己也在升級,現在看到的是它的4. 0 版本。比擬前面三季,在放肆表達的外貌下,第四季的《奇葩說》更著力探討青年人真正的思想困局,金句少了,更多是想要為 90 后、 00 后帶去少一些戾氣的解決方式參考。
2
我們常說這個時代是一個感官主義主導的視覺文化時代。圖片、聲音和影像都是誘餌,尤其是影像,統帥了受眾。以此維度不雅觀之,奇葩說是感官主義主導下的互聯網理性狂歡,關于狂歡,此前我專門有一篇文章解讀:走心走腎、嚴厲辯論,《奇葩說》其實是一場都市中產的敘事狂歡
這里,我想站在受眾角度,談一談奇葩說是如何通過解構中國式關系,讓節目受眾達到虛擬性參與,并引起個體自身紛繁復雜的不雅觀點和行為的。
我蠻贊同武大新傳院孔鈺欽從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入手分析。她說,在辯手或主持人、嘉賓結合自身經歷進行不雅觀點闡述時,其實某種程度上就是在用“故事”的鋪陳去影響受眾的選擇和判定。差別的故事,可能對受眾產生的有意識、無意識的影響也就差別,也就產生了千差萬另外不雅觀點、視角和立場。在這個多元的意見碰撞場中,受眾會從中找到所謂“本身”的影子。
受眾有意識的參與和無意識的虛構性參與都會更多更強。好比受眾在不雅觀看《奇葩說》時,選擇立場進行實時投票時,受眾立場的改變或者搖擺,也就是節目中的“跑票”形式,某種程度上就是人格結構中“矛盾”的具體化。心理層面的虛構性參與導致了行為層面上投票、評論互動的有意識參與。
嘉賓和選手身份的尤其性,更加刺激了受眾的參與。 6 月 9 日這期,高曉松回歸了,蔡康永說這會激發他的斗志。假如說蔡康永是感性的人文關懷,那么高曉松即是與其對立的理性關懷。
在《曉說》和《曉松奇談》中,高曉松更多是點評歷史,但坐在辯論隊隊長位置和嘉賓位置的高曉松,可以不留情面地點評選手,也可以毫無保存地表達他對肖驍從蛇精男成長為辯手的夸贊,以此展現有血性的一面。對肖驍來說,在奇葩說的經歷勝過了他讀四年大學,對高曉松來說,修煉成網紅的路上,《奇葩說》承擔了與《曉說》完全紛歧樣的功能。
上一篇:121.互聯網+實現遠程協商
文章地址:http://www.meyanliao.com/article/online/5444.html